《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由刘震云著作的小说,很多网友都看过刘震云写的《手机》和《我叫刘跃进》,小编这里给大家带来了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一起来看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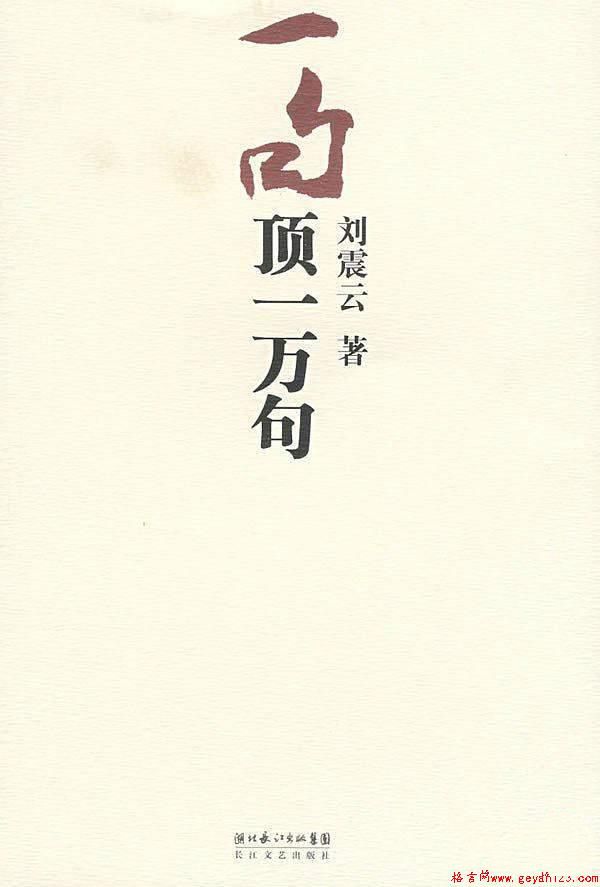
01
全文在牛爱国的一句“不,得找”处戛然而止,而迷题还没解开,烦恼还没消散。初时疑惑,细思明白,无论找到章楚红与否,那重要的一句话都再也无法找回,毕竟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说得来的变的说不来,说不来的又变的说得来,心情、性格脾气已不再,昔日友人的情意也变淡泊。书中的人物们错过了心爱的人、更换了自己的名字、丢失了重要的那一句话,都孤独地衰老、孤独地试图挣脱孤独、孤独地迷茫着前路、孤独地踏上旅途、最后孤独地死去。我认为刘震云描写的是永远孤独永远有缺憾甚至有点荒谬的人生常态,而书的导向却是积极的,永远去寻找、去试图弥补缺憾、以及在未来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本书的叙述方式很有趣,枝枝节节地牵扯出许多人物打酱油,隐晦地展现着时代、观念的变化,并且配角们其实也是和主要人物一样始终有缺憾、在寻找着什么的人,所以丰满立体的感觉就特别强。感觉书的结构像巨大蜂巢,作者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两三个毗邻的六角形小室给我们看,有种小小的广博感。以及全书基本明面上都是单线叙事,几个不同的主要角色主要剧情之间互有补充互有留白,交叉地好棒啊。也有很多人物的故事就这么无疾而终了的,真的很好奇杨百业杨百利等等人后来的故事,但就像生命中大部分人只是匆匆路过一样,这些人也只是 故事的过客,巨大蜂巢的另外一些小室吧。
最后,像《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故事是讲不到真正的结局的,一句话永远会牵扯出一万句话,故事永远有后代在延续,永远在陕西、河南乃至全中国全世界上演着,这样的戛然而止,大概是告诉读者故事已不必讲,心存希望、继续寻找就好了罢。
02
看完这篇小说,其实并没有太明白为什么标题要写成《一句顶一万句》。小说叙事的风格,很像学生时期读过的《墙上的斑点》的意识流小说,从一个人说起,然后是他的街坊邻里,七大姑八大姨,老婆孩子,各种关系。
原来没看过以这种散式结构的小说,型散神不散。
上篇出延津记,主线为杨百顺怎么成为杨摩西,又成为吴摩西,最后以罗长礼做结。杨百顺天生不是爱说话的人,也不太会说话。
杨百顺:成长期,和家里闹翻,出走,各种找活路干,稳定不下来。从小的理想和最喜欢干的事情是罗长礼喊丧。自己不太爱说话,因此在杨家不会给吆喝卖豆腐。离开杨家庄。
杨摩西:遇见曾神父,有了信仰(假的),改了名,想稳定,歪打正着进了县政府,种菜。神父传教,跟他说话,他并不喜爱听,也听不懂。
吴摩西:婚姻,入赘,有了继女。继女巧玲能和他对话,他也喜欢跟巧玲对话。
罗长礼:老婆私奔,养女走丢被人拐卖。离开延津。
下篇回延津记,主线为牛爱国,牛爱国是杨百顺继女巧玲的儿子,也就是杨百顺的外孙。故事到了牛爱国这里,已经过了50年的光阴。时代变了,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牛爱国有自己的生活,最终是母亲曹青娥一直的念想,指引着牛爱国回到延津。
人做的很多决定,都是意气用事的结果。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纽带,也就是一两句话的事。一句顶一万句,很多时候一句话,发挥的作用就是很大,一念之间。
03
吴摩西本不叫吴摩西,他是延津县卖豆腐的老杨家的二儿子,后来和家里断绝关系后投奔了意大利传教士老詹,老詹给他改了名字叫杨摩西。不同于《出埃及记》里的摩西,这时的杨摩西连延津县也未能走出,不过,改了名字的杨摩西到自此和他爹没有甚么瓜葛了。后来到了县城,卖馒头的寡妇吴香香看到他在县政府种菜,便有意招赘他,只不过要改姓吴,杨摩西这次又去问老詹的意见,老詹倒是支持了他的决定,只不过这次他是以詹大爷的口吻来说的。于是,杨摩西便成了吴摩西。吴摩西后来因为丢失了巧玲,便再没回过延津,而到了宝鸡。到了宝鸡之后,吴摩西又不叫吴摩西了,他叫罗长礼,一个被众人遗忘的会喊丧的人。
改了这么多次名字,只有罗长礼这个名字是他自己最后选择的,之前的并非出于他自己。对于老杨的彻底反叛就是从改名为杨摩西开始。只不过改名为杨摩西并非出于他自己的虔诚,而是为生计所迫。而在和老詹的接触里,杨摩西若真是对主虔诚,那也是为老詹的人格所触动的,显然,这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不归上帝。有趣的是,以改名为界限走出家庭的杨摩西又要以改名为节点进入到寡妇吴香香的家庭,只不过在这里值得他精神上留恋的只有吴香香的女儿巧玲而已,而这个五岁的小女孩也恰恰是能够和吴摩西互相有话说的人,也是因为她,我们才会在她的后半生了解到吴摩西的后半生。吴摩西离开延津也是为了去寻找被老尤拐走的巧玲,走了很多地方未曾寻得,走到宝鸡地界反倒心结解了,便在这里落脚下来了。这种感觉,就像老汪当年因女儿灯盏的去世而一路走到宝鸡便落脚下来吹糖人一样。只不过,在去宝鸡的火车上,异乡人再问吴摩西叫什么的时候,他说他叫罗长礼。
喊丧本就是一种发生在葬礼上的行为,它看着是对死人的表达,可看到它的却仅仅是活人。喊丧的滑稽恰恰在于其表达对象的错位。然而错位却是有戏剧色彩的,人和人之间也是如此,错位总会迸发出很多的故事。其中有一种最被压抑的错位,就是说不上话。因为意识到很难被人理解,无非就是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最尴尬的便是,当你在这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倾听者倘若有些耐心还能含混过去,无耐心者看来,倒与观看喊丧是无异的。于是,一次两次的挫败感会让人逐渐认识到,怎么说,有些话总不会被听懂,如同杨百利的喷空只有同样有想象力的人才能理解其快乐一样?失去了巧玲以后,吴摩西选择了一个喊丧者“罗长礼”的名字,往后的岁月不知他有多少的歇斯底里,也是在后半部分,年迈死去的巧玲久久不能忘记这位叔叔。在那之前,即使是给他带了绿帽子的吴香香,也会与隔壁的高老板大战几个回合来诉说着自己。吴摩西的前半生,就是在寻找说得上话的人的路途中。
看着吴摩西的故事,脑海中却跳出来了祥林嫂,祥林嫂是慢慢喜欢唠叨但又逐渐不被人倾听的人。祥林嫂的孤独就在于,她(它)被解读为饱受着父权,夫权,族权,神权四座大山压迫的人,做了新思维的刍狗,殊不知,这样的宏大叙事恰恰让我们忽视了人有被倾听的需要这一基本事实。抱着对于祥林嫂的同理心,杨百顺到罗长礼,这个名字的变化,道出的则是再也很难有说得上话的人的孤独。而这似乎是我们生活的共相,精神上的孤独并非只有致力于沉思生活的人才会有,这些孤独者恰恰就是最普通的人们,他们有很多甚至也叫不上名字。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少年,似乎成了人们的宿命。于是,一切反道德的形式似乎都蒙上了与宿命对抗的色彩,被以讹传讹时想杀人是如此,与已婚之妇通奸的情感纠葛也是如此。这些事情难分对错,也只是在几位上年纪的人口中所说,过日子是往后看而不是往前看的。只不过,这到底是我们的选择,还是我们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