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总会有一些恐怖分子来破坏人民的和平和安定。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小说《群魔》就是探索恐怖分子的内心活动的一本书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小编这里整理了一篇网友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一起欣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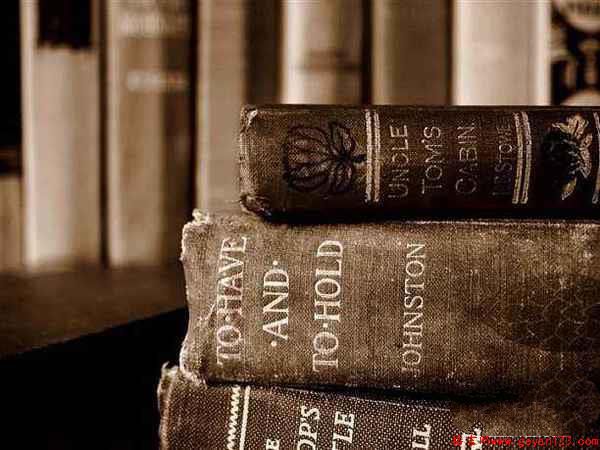
考完试,突然想起了《鬼》——之前一直不敢看陀氏的这部小说,阴暗,可能是唯一合适的形容词。但
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厌倦了一切,有什么能让我更消沉呢……
但是我错了。卧在病床上,我不禁猜想这次的病与这本书或许还有些关系: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联系永远是被低估的。身体忽冷忽热,最难以忍受的是一阵阵的恶心与眩晕,好像失去了一切欲望,只想昏睡过去——也算是理解这本病态的书的代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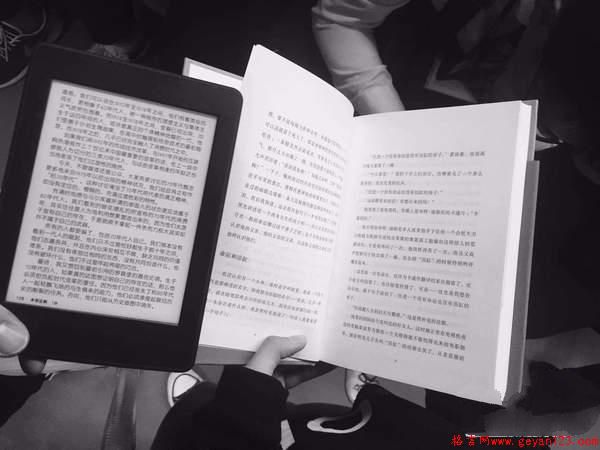
“我从来不会有愤怒,也不知羞耻为何物;所以也从来不会有绝望。” 这样说的斯塔夫罗金最终也自杀了。他的这一决定,或许也的确如他所说不是出于绝望,而是一种彻骨的厌倦之感,他感到生命已经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了。由于失去信仰而受苦的他迷失了,分不清行善与作恶。“我仍然希望行善并且因此而感到快慰;与此并行不悖,也愿意作恶并同样感到快慰。”在年轻时荒淫的生活中,他什么也找不到,反而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而对于妻子和莉莎的死,他知道自己负有良心上的罪责:明知凶案要发生,却不出面阻止。自然,没有人会因此而逮捕他,于是他成了自己的审判官。可是,每次向善的愿望一出现,他就嘲笑自己,他总是以蔑视一切,挑战一切,甚至否定一切的高傲姿态面对这些念头。甚至对于神,他也玩世不恭地说: “要熬兔汤,需要有一只兔子,要信仰上帝,需要有一个上帝。”矛盾的是,他并不否认上帝是必要的。用基里洛夫的话来讲:”假如斯塔夫罗金信教,他不信他信教,假如他不信教,他不信他不信教。”他自己却意识到这种否定浅薄,萎靡,毫无力量,于是厌倦到来了:“我知道我该把自己杀了,把自己像可恶的虫豸一样从地面上消灭掉。”他蔑视一切,但最蔑视的却是他本人,尼古拉 斯塔夫罗金。

基里洛夫的自杀就是出于相反的原因了:这是他的理念,他的思想。他的困境倒是与尼古拉相同,饱受两种信念的无法统合之折磨,然而不同的是,他是严肃的,因而形而上的问题在他看来必须诉诸极端的解决办法。“你们怎么不明白,那是足以自杀的一个理由呢?”这无神论的逻辑或许有些疯狂,难以被世人理解。“假如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了。……我的神性就在于独立。” 自杀是一种抽象的自由声明: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们,反之,我们对上帝的意志丝毫不能违抗。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自杀的方式呢?仅仅为了将世人从盲目而虚假的希望中拯救出来,正是这希望使得人们诉诸上帝:”人为了不自杀才创造出上帝。”基里洛夫没有疯,他只是性格中有那么一种冰冷的,非此即彼的绝对感,他甚至认定一切皆善——即使是斯塔夫罗金那样的人也是好的,然而他这样想仅仅因为他已经认定:存在是虚幻的。他体验过几秒的“永恒的和谐”:世界亲切而实在,那种快乐超越了爱,超越了感动,超越了宽恕。他知道只有在这种和谐中才存在幸福,而没有凡人能生活于这和谐中,它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他“以起诉人和担保人,法官和被告无可争议的身份,谴责这自然”,因为自然使人们生来不能幸福——“我判处自然与我同归虚无”。

对于这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或许藏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渎神的伊凡以疯狂告终,而阿辽沙却对孩子们宣告:我们死后会重逢,会高高兴兴地交谈所发生的一切。自杀与疯狂于相信不朽与快乐的人们有什么用呢?世人继续其希望,并不能理解他们的判决。然而,阿辽沙是清醒的,并非无知的世人。也许,面对荒诞的人生,除了自杀之外,还有另一条通向永恒的路,更火热,充满了爱的勇气;但是无论“热”还是“冷”,二者都让我觉得亲切。
